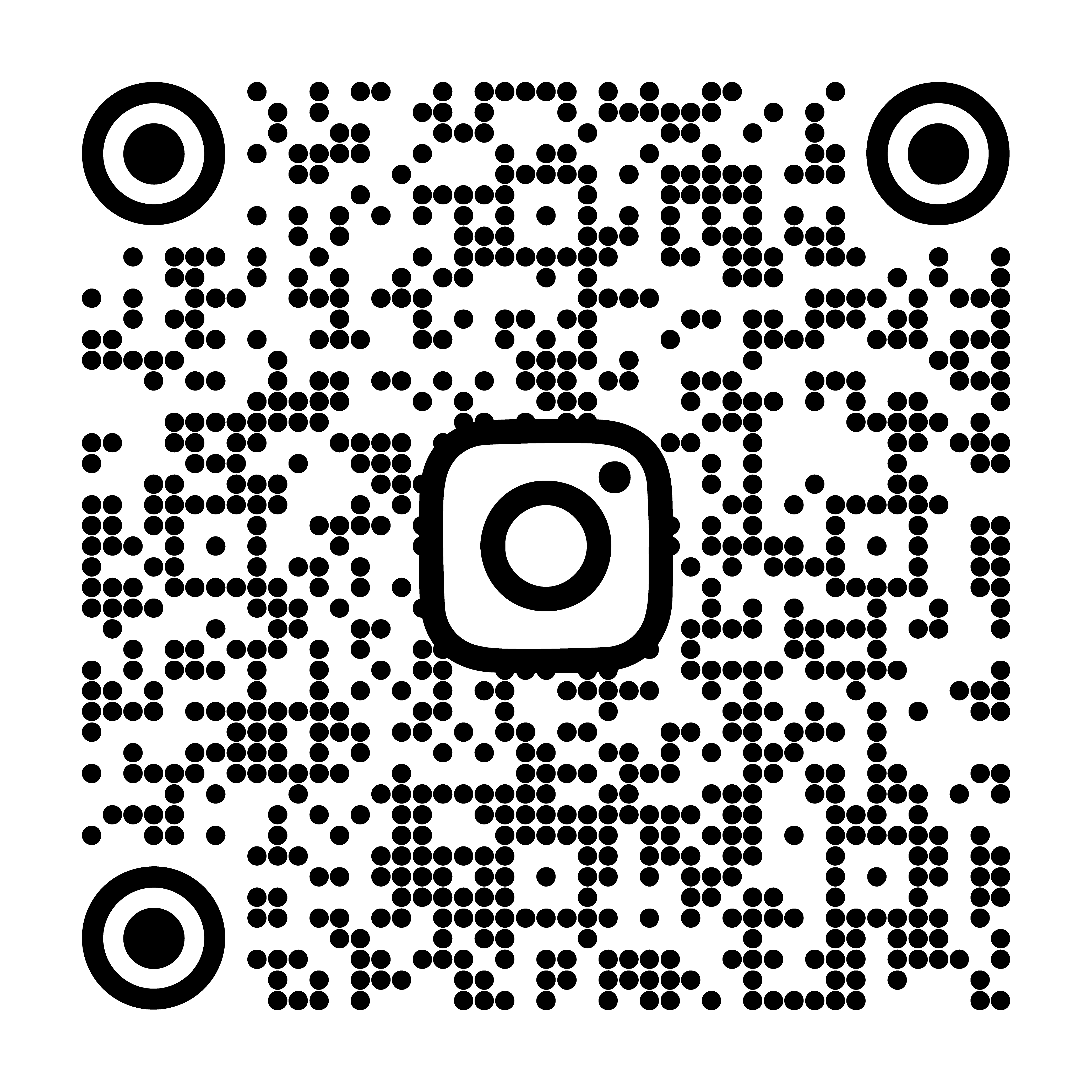作为一名创作者,我不是严格意义下的艺术家,或者,我不是传统意义下的艺术家。2014年开始,我成为艺术家许哲瑜的创作伙伴,十年来参与十件录像作品的概念发想、脚本编写、调研访谈、拍摄现场、展览规划与国内外的作品发表现场,同时,这些年间,我也是一名编辑、记者、研究者,参加其他展览研究和文章书写。这些混杂的身份大多时候并不让我困扰,往往使我迷惘的,是这花花当代艺术世界里,创作究竟是什么?它又能带我们去哪里?2019年开始,我赴阿姆斯特丹就读博士班,创作拍档许哲瑜则是陆续于比利时根特HISK、法国图尔宽Le Fresnoy、荷兰阿姆斯特丹Rijksakademie此三地进行艺术家驻村。这篇文章中,我试图以创作者的视角记下这些我们一起移动与驻留的经验。
启程:向宇宙下订单
2018年的某个夏日,我们收到了来自比利时根特高等艺术学院HISK两年驻村申请的面试通知。当时,因为各自生涯规划改变,我们试图寻找位于欧洲、并且驻村时程较长的申请机会,曾经在荷兰待过一段时间的艺术家好友吴其育给了我们一些机构名单,位于比利时根特的HISK就是其中之一。在申请之前,我们已听闻艺术家吴其育、许家维几年前在欧洲Post-Graduate艺术机构的驻村经验,也因此对于两年期的Post-Graduate艺术驻村项目有比较多的认识。类似的Post-Graduate艺术驻村机构,在法国、比利时、荷兰都有,主要提供具有硕士学位以及实务经验的艺术家进修,大多以两年为主,驻村结束之后也会领到符合该国教育部认证的学历证明──简言之,硕士以上,博士未满。虽然如此,但是在两年的驻留过程中,完全以实务支援为导向,没有需要修习的学分与课程,因应不同机构资源会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援、工作室与制作预算,也因此吸引许多来自各地的艺术家提出申请,竞争激烈。
面试前,我们沙盘推演了许久,视讯面试时由我担任中英文口头翻译。因为时差,视讯面试结束时台湾正值午夜,我们爬上工作室的天台,夏夜晚风伴随着些微闪亮的夜空,纾解了我们既兴奋又忐忑的心情。许多天后,手机响起一组国外的电话号码,是HISK从比利时打过来的录取通知。于是,2019年1月,我们抵达根特,开启了两年的驻村计划。
HISK每两年会雇用一位策展人,负责规划艺文机构参访、主题研讨讲座、邀请专业人士来艺术家工作室参访、策画年度展览等。每个月为期一周、密集安排的Studio Visit,成为最令大家重视的活动之一。每月的这一周,平时在不同城市跑来跑去的艺术家们会回到根特,由HISK邀请来的艺术专业人士也会造访根特住上几天,轮流到每一位驻村艺术家的工作室中进行一对一的作品讨论;这些艺术专业人士包括策展人、艺术家、学者、研究者、美术馆从业人员等,地域不限。对于我们而言,受益良多,一方面我们过去的艺术教育养成都是在台湾,比较少有机会针对作品概念进行跨文化语境的深入探讨,另一方面则是毕业离开学院之后,若非凭借展览机会创造与艺术专业人士的对话契机,几乎只能埋头苦干。当然,在Studio Visit中因为语言问题而鸡同鸭讲,或是对于形式表现意见不合而暗潮汹涌的情景,也不在少数,也常遇到前辈艺术家抱持轻松闲谈的心情漫聊起生活、亚洲、或是在不同国家的展出经历,最有收获的应是在与巴西圣保罗双年展策展人聊完之后,收到参与圣保罗双年展的参展邀约,让我们有机会第一次造访南美的当代艺术重镇。
工作室参访之外,与同期驻村艺术家之间的交流也成为我们理解不同国籍背景艺术家生活、创作、移动的状态,甚至也见识到了艺术圈里「身份政治」的运作对于艺术家职涯发展的具体影响。
在路上:迷雾中打怪
2020年秋日,我们跳上火车,从根特出发,前往比利时与法国边境,准备穿越国界抵达图尔宽,总车程大约一小时。HISK第二年驻村中期,我们整理了近年的录像作品,向另外一个同样是为期两年的驻村机构、以电影制作与科技艺术闻名的法国当代艺术工作室Le Fresnoy – studio national des arts contemporains提出申请。收到面试通知之后,我们咨询了多年前曾在Le Fresnoy驻村的艺术家好友许家维,他慷慨地分享面试经验,几乎百分百正确猜题,可惜我们临场发挥不善,在公布入选名单那日仅有候补资格,直到夏末之际,才再次收到机构方通知候补成功。
跟HISK的艺术家成员全数来自不同国家的惯例不同,Le Fresnoy的名额有一半保留给法国籍艺术家,至于另外一半名额也会视法语能力为加分标准。有别于HISK提供艺术家工作室空间作为一系列规划活动的实践基础,Le Fresnoy则较类似电影制作单位,在第一年与第二年的驻村期间各自提供一笔作品预算与一位专业电影制片人,让艺术家完整执行拍摄计划。因为涉及预算与制作,再加上Le Fresnoy的电影工作方法,制作前期有大大小小的技术会议与口头简报。在逐渐确定创作概念、拍摄工作时程、展示形式之后,由Le Fresnoy总监为首组成的委员小组会举办评审会议,每位艺术家需要在评审会议中以口头报告创作计划,并且回应针对创作计划的相应质疑。评审会议之后,会公布评审结果,若未通过者须再次提案,或者Le Fresnoy有权利解除制作合约。这也是每到年度中期,艺术家们焦头烂额的工作重点,过了这一关,才能实际启动拍摄工作。
Le Fresnoy作为法国电影艺术起家的重要机构,硬体与软体设备都是一流,不过更具特色的是每一年机构会邀请六位极具国际声望的电影导演、当代艺术家、剧场导演入驻机构,与艺术家一对一媒合担任其导师(mentor),提供创作构思阶段的讨论;不仅驻村艺术家需于该年度完成一件作品制作,六位艺术导师也会在机构提供的资源下,进行自己的拍摄计划。在我们两年的经验里,艺术导师的角色与其说教导艺术家如何创作,亦师亦友的交流关系更令人感到难忘,尤其当我们的创作题材大量涉及台湾本地的历史和情境时,时常在讨论中得以将自己拉出一段距离,审视创作的思维和方法。
继续航行:海拔负11公尺
2021年末,按下电脑萤幕上的「送出」键,完成上传了申请阿姆斯特丹Rijksakademie的报名表,这是我们第三次填写同样一份表格,也是最后一次能够把握的机会,Rijksakademie在近年新增了一项报名规定:一位艺术家仅能有三次申请机会,这项规定为的是管控每年庞大的报名人数。从根特HISK到图尔宽Le Fresnoy,眼见已经要在欧洲待了四年,我们决定用上最后一次申请机会。出乎意料地,我们收到面试通知,结束面谈之后经历了胶着的等待期,最终收到正面回音。
曾经待过Rijksakademie两年驻村项目的台湾艺术家包括崔广宇、陈滢如、吴其育、罗晟文,许家维则是在同时录取Rijksakademie和Le Fresnoy的情况下,选择前往后者。在荷兰,类似的Post-Graduate驻村机构除了Rijksakademie之外,还有同样位于阿姆斯特丹的De Ateliers和马斯垂克的Jan van Eyck Academie,这三个艺术机构除了提供艺术家工作室空间、专业的技术工房(印刷、木作、金属、陶艺、绘画、媒体等),也会赞助每月生活津贴和年度制作费,相对优渥的驻村条件是吸引艺术家前来工作的原因之一。与法国的Le Fresnoy相同,Rijksakademie的名额一半保留给居留注册于荷兰的艺术家,另一半则开放给其他国籍的艺术家。两年驻留期间,机构也会定期组织Studio Visit,邀请艺术家、作家、跨领域专书作者、独立策展人作为创作顾问(advisor),提供驻村艺术家深入讨论创作计划机会。虽然在驻村两年期间,Rijksakademie不会要求艺术家以作品作为成果,但是每一年度的尾声,Rijksakademie搭配阿姆斯特丹艺术周而盛大举办的「开放工作室」活动,近五十个艺术家工作室将对公众开放,其布展规模和参观人潮堪比美术馆展览开幕。
整体而言,可以把Rijksakademie看为欧陆当代艺术如何操作、运行的部分缩影,它涉及国家资源的巨量挹注、艺术市场和藏家的参与、双年展机制的舞台、专业技术团队的支援,当代艺术家的专业化养成。在这层层运作关系中,很多时候,艺术家的角色已经算不上是最重要的。运作模式可以从Rijksakademie的组织分工略窥一二。驻村初期,机构会邀请一群收藏家前来工作室与艺术家进行交谊晚会,透过导览工作室和轻松的酒会,鼓励收藏家出资赞助单一艺术家在驻村期间的工作预算,至于是否顺利媒合,全看缘分,不过,另有Rijksakademie内的策略发展部门采取较主动的方式,它们对于各个艺术家母国艺文补助的环境和条件早已有初步理解,也会咨询驻村艺术家,提供能与Rijksakademie合作的潜在艺术基金会名单,在艺术赞助网络连结的策略上主动也灵活。今年,洪建全基金会便在Rijksakademie的邀请下,提供我们驻留其间的制作赞助。
一本复杂的地图
写文章的此刻,我们正工作于2023年Rijksakademie的开放工作室,全驻村单位从上到下无一不为此忙碌着,或许将还有人赶工到开幕前的最后一刻。如果说开始于2019年,预计2024年结束的艺术机构驻村经验,能说得上什么体悟,那便是对于当代艺术建制化本质的实务认识。为什么当代艺术家想要/需要驻村?为了不同文化背景的环境中寻求创作灵感?为了建立人脉网络,以便获得更多艺术计划与展览的机会?这些目的纵使可能透过异地驻村的机会达到,但是不透过「驻村」机制,直接在他方生活,也可能有相似的际遇。在当代艺术还尚未如此机构化、系统化时,艺术家难道不是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待多久就待多久?
这些年的艺术机构驻留经验使我们越来越认清,当代艺术就如Tom Holert所言,与其将之认定为一种特定的形式风格或创作方略,当代艺术是由全球艺术资本(文化政策、美术馆、双年展、博览会、收藏家、基金会、艺术学校、学术生产、艺术机构……)不断形构、变化的结果;我会对自己说,别太天真,当代艺术有原罪。认清这样的事实,终究,当代艺术创作对我们而言是什么?如果,创作真的有答案,我想象着,那也将不再是任何理论学说、任何文化责任、甚至任何意识形态能够解释的。它必然抽象到非常简单。
如果一切的航行有方向,我想就是在复杂的地图上找出那样的答案。